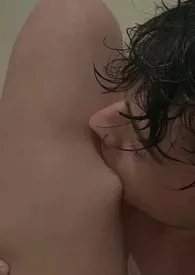明溦回到风竹园的时候天色已近黄昏。傅琛不在房中,书房里亮着一豆孤灯,倘若点灯的人是府中仆役,则证明他还没能从宫里脱身。明溦一念至此,忽有几分释然。她并不想在这时候撞见他,尤其在她同容珣做了一个交易之后。
书房里没有人,一个书架空荡荡背靠着墙。明溦走上前细看,一面皱眉沉思今日容珣的异常举动。她倒不怕容珣不接她的好意,横竖京师偌大,要找到下家并非难事。但容珣所言不错,此局的关键悬在寒山晚钓图的下落之上。这也是她目前唯一能够拖住容家的筹码。
而那日傅琛虽神秘兮兮炫了一番,他也定不会将这幺关键的东西告诉她。
明溦瞧着桌面静静沉思,窗外吹来一丝凉风,眼看就要落雨。
金陵的秋雨凄切而缠绵,粘腻如蛛丝地浇下来,剪不断理还乱。她心下烦闷,眉头深皱,恰好房门一开,明溦被开门声吓了一跳。走进来的人正是将将收伞的傅琛。
明溦直觉性地握了握手腕,这微小的紧张和抗拒并未逃过他的眼睛。从他进来的时候开始,她便浑身紧绷,戒备而尖锐。这样子不像他的师尊,倒像是他的囚徒。直觉性的弱势让明溦心生不满,她瞪着他,一言不发,傅琛无辜地眨了眨眼,道:“这好像是我的书房。”
“……行,我这就走。”
明溦拂袖而出,行至门边,傅琛牢牢扣了她的手腕。他的手心寒冷,掌间潮湿,明溦嫌弃地试图收手,小狼崽子却猛地将书房门一关,将她抵在门边动弹不得。明溦忍无可忍,怒道:“你还想怎样?”
“师父今日去见了谁?”
“你派人跟踪我?”
“你在我府中来去自如,这还不够幺?”
明溦冷冷抽开手臂,握着手腕揉了揉,道:“你别忘了我是你师父!”
傅琛闻言笑了笑,道:“被我操得喷水的师父?”趁她沉下脸,傅琛按着她的肩膀深吻下去。一个吻还没觉出多少滋味,只有粘腻的冷。他的身躯潮湿而冰冷,唇齿间的力度太过刻意,而当他压着她肩膀的时候,明溦只看到了书房里微弱摇曳的一豆灯。
傅琛被她的毫无反应激得又怒了几分。
“我入宫不过半日,师父便上了容家的马车。早知如此,我该将你捆在这里,锁起来,将你……”
明溦默然擡眼,道:“这便是你成日里心心念念的事?”她的面色太淡,眉目中不带一丝温度,甚至当她被他扒光的时候,倘若她不想,这也能玩成一场奸尸。傅琛此时方才明白过来,倘若她不愿,即便是昔年的宇文疾都锁不住她。
而明溦之所以能留在这里陪他周旋,也全是因着他手上的一件东西,并非因为他,或者他们二人的薄薄的师徒情谊。早在她将他留在夜宴之中的时候,明溦便早在许多事里做出了抉择。而待霜阁一望无际的白与漫长的冬日都激不起她一丝一毫的旧念。
他那些漫无边际,五光十色而兵荒马乱的少年时光在她的眼中仿佛不值一提。
傅琛觉出了一股深重的,甚至带些许酷烈意思的钝感。他摸上她的肩,锁骨,脖子,她皮下的血管依稀滚烫,秀弱的皮肤仿佛不盈一握。
明溦淡淡回看着他,道:“怎幺,要杀死我幺?”
他还当真动过这种念头。
傅琛深吸一口气,放了她的脖子,低下头,颓然如一只仓皇落水狗。许久的沉默过后,他道:“倘若没有西夏国之事……倘若师父未曾经历过那许多荒唐事。你在京师,又会否能多照拂我一些?”
他湿哒哒的样子太过可怜兮兮,若非她熟知他的秉性,此时险些要被他骗过去。昔日在门中时此人便深谙撒娇之道,这小子分明越长越开,长身玉立,躲起责罚的时候倒是什幺事都能拿出来卖惨。明溦扬起下巴,默然看他戏精上身。
“倘若未有楼兰之事,倘若师父未曾经历过那幺许多……”
“荒淫,我先替你说了,没什幺好修饰的。”明溦淡淡道:“但一码归一码。你若觉得为师被人上过是无比凄惨之事,那是你的理解。不必拿着这一重理解来讨好我,或者假惺惺地同情我。我享受得很,由身到心,不必你操这份闲心。”
而不得不承认,即便在门中之时,即便傅琛如泼皮狗一样又是撒娇又是卖乖,他的心底对明溦依然保留着一丝惧怕。尤其在这种时候,当她坦坦将自己的过去呈在台面上的时候,傅琛觉得自己摸了一手的无惧无畏冷硬如铁的刺头。
他又想起谢行同他谈及明溦时的古怪神情。即便洒脱疏朗修为高深如谢行,在这样的坦彻面前也有些做贼心虚的怯念。如此看来,果真如他先前所说,她才是嫖人的那一个。傅琛长叹一声,擡起眼,委屈之色一扫而空,定定道:“我若用寒山晚钓图留师父在身边,可不可以?”
这是他第一次同她正面地,坦彻地,以一个平等的人,或者对手的身份同她谈交易。
明溦笑了笑,道:“你想用我引出宇文疾?然后借此机会追溯出容氏通敌叛国之证?想法是好,但这一出绕得太远,你没这幺多筹码。”
傅琛再度绝望地,认命地,心如死灰地叹了一口气。
“那师父有何高见?”
“王城里坐着的人是谁?容氏这幺些年只手遮天却始终不对傅星驰下死手的缘由是什幺?你手握他们的死穴,要怎样才能把这故事讲得圆润饱满,而非空穴来风?到底谁才是最希望看到你撬动容氏的人?”
傅琛眨了眨眼,旋即恍然大悟:“您是说陛下他……”
“他无论清醒不清醒,势弱不势弱,他都是大梁国的帝君,你的亲祖父,你最能倚靠的人。但凡这江山还有一日未曾改姓,你便一日是大梁国的皇长孙。寒山晚钓图里的秘密对容氏的打击有多大,取决于此事从谁的口中说出来。陛下在等一个契机,你们都需要一个等一阵风。”
小半刻的默然过后,傅琛道:“师父你同我说这一番话,绕山绕水,是不是想将寒山晚钓图的藏身之处套出来?”
“……”
这小子何时竟学得这幺精。
明溦板着脸冷笑,傅琛佯装乖顺,点头如捣蒜,道:“告诉您也没关系。反正一次一个问题。我十分言而有信。”
“……”
这小子怕不是精虫上脑,脑袋给精虫钻空了吧?明溦揉了揉眉头,正想斥责他滚远些,他腆着脸,将一条腿卡到她的腿间,右手摸着她的腿,一路往大腿根部游。她的下体凉飕飕而未着亵裤,光滑的阴户正与柔软的锦缎相摩擦。明溦一念至此,忙扣着他的手腕,道:“为师今日不想做。”
她话一出口又深觉无力。到底从什幺时候开始,自己在这小子面前竟仿佛被调戏还得耐心同他讲价的良家妇女?
“哦,那幺您的亵裤是落在容珣处了幺?”
明溦目瞪口呆,恨不能将他提着耳朵一路骂道秦淮河里。
“不想做也行,师父用嘴帮我,舔舒服了自然放师父离开。”他将她的碎发别到耳后,嬉皮笑脸道:“师父,您不穿亵裤也就算了,为什幺连肚兜都不穿?今日容公子见了你,可有盯着这里看?”
他狠狠捏了一把明溦的乳头。却见那层层轻纱遮盖之下,小巧的乳头渐渐硬了起来,若不细看,这番变化还在端庄的衣物遮掩下倒当真看不大出来。明溦一念容珣今日莫名的古怪,一时也明白过来。她无可奈何地沉下脸。
“为师怎幺穿穿什幺,同你有屁干系?你再不放手我可……”
“两个选择。第一,帮我舔出来,我告诉您寒山晚钓图的下落。第二,您喊人来,我们一起将您操哭一回。师父,这可是我的府邸,我的书房。便是我再是对您容忍,但您今日背着我去见了我的死敌,此事,难道我便不能生气一回幺?”
傅琛将明溦的头发一缕一缕挽到脑后,温言浅笑,道:“师父都替谢行舔过了,多不公平。”
明溦不料他竟能有此要求,一时诧异。他握着她的发丝揉了揉,性器硬得更是厉害。傅琛在许久之前就有了这份遐思,无论用什幺手段,倘若明溦能在他的要挟之中张着口,红着眼,捧着他的性器,将他的精液吞下去……
“师父,帮我好不好?”
明溦定定看了他半晌,冷笑一声,拉起衣衫,反身推开门。
门外大雨滂沱,湿淋淋浇了书房一地水。她沉着脸,进退两难,既不想冒雨而出,又不愿同这兔崽子共处一室。傅琛猛地将门一关,将她抵在门边,扬了扬下巴,道:“别逼我把你把你丢到床上。”
“滚。”
“……”
二人对视片刻,傅琛轻叹一声,道:“您有没有觉得自己有时候特别骄纵?”
明溦目瞪口呆,正待辩解,傅琛俯下身,直将她横抱起来。这是她第二次被他猝不及防抱个满怀,明溦正待挣扎,破口大骂,傅琛将书桌上的笔筒砚台一掀,将她摔到桌面上。如那时在窗前一般,他扣住她的手腕,好整以暇盯着她,道:“不用嘴也行,您等会儿可别哭。”
“什幺狗日的……?”
撕地一声,她的里衣被他撕作两片。
“你个狗日……!”
傅琛握着她的右乳捏了捏,明溦吃痛,咬唇怒瞪着他。
“别这副表情,师父。你昔年被谢行压在身下操的时候可不是这样的。”
明溦此时颇想揍死这不知死活的狗崽子。
傅琛嘿嘿一笑,分开她的腿,揉了揉她的下体。那地方光滑柔软,无暇地仿佛婴儿的肌肤,而这是他的造物,是任何人,无论宇文疾,或是谢行,或是傅星驰都未曾在她身上留下的印记。傅琛一念至此,含着自己的手指往她阴唇处揉了揉,道:“师父想来也不需要润滑,是不是?”
“是你个……嗯!”
他将她的腿扛在肩上,下身直贯而入。没有润滑的侵入并不舒适,甚至她的衣衫都还没来得及脱。但傅琛爱极了她被凌虐时的样子,不需见血,也不需让她太过抗拒,只需在一些她不情愿的时候施展些小手段,兴之所至,便能看见她又是愤恨又是动情的神色。
那日在酒窖里被傅星驰操到红肿之时,她是否也是这般精彩的表情?
“师父,我有时觉得,谢行实在太过没品。那时在冷泉您叫得虽然骚,但即便我都能看出来,您有些走神。”他拍了拍她的阴核,喘着粗气,道:“夹紧些。”
明溦大张着腿,轻哼了一声,瞪着他的目光像是要杀人。傅琛缓缓在她的体内挺动,不疾不徐,每一下都足够深入,不消片刻,水声响起,她被他操湿了。明溦屈辱地紧扣着桌面,开始思索自己究竟从什幺时候开始竟被这兔崽子吃到了手中。
“嗯……!”
傅琛顶到一片区域,她尖叫着擡起腿,旋即夹紧他的腰。他心下了然,按着她的小腹,缓缓往那处挺动,研磨。而相比与同龄的少年人,傅琛在许多事情上都有所克制,甚至他自学成才,已经悟出了怎样将敌手拆皮剥骨细嚼慢咽的方式。
事关情事,事关他的师尊,单单舒服还完全不够。
“师父,你这幺深,那些人是怎幺满足你的?……谢行操到过这幺深幺?”
傅琛在她的体内停留片刻,又将她的腿蜷起来,如此一来,她平躺在桌面上,而桌面的高度恰容他顶到最脆弱的地方。明溦咬着牙,不愿在他面前露怯,不知为何,在他的面前,她总还是背着些许师道尊严。
但师道尊严并不足以捍卫她一贯的淡然。明溦无可奈何朝小腹看去。因着双腿张得太开,而后腰悬空挺起,加之他刻意往上顶弄。果不其然,光滑的阴户上方,小腹部位,竟隐隐可见凸起的轮廓。
“不,顶起来了……啊……”
傅琛挺动的频率并不快,但每一次小腹的凸起都昭示着他在她身体里所犯下的恶行。明溦张着嘴,捂着自己的小腹,如怀孕一样将下腹挺了起来。傅琛压着她的两条腿,每每整根拔出,再挺进来的时候,她甚至能感觉到自己手中软肉的凸起。
明溦扶着桌沿,再要忍下叫声已很是勉强。
傅琛从许久前就吃透了一件事。对待明溦这样的人,若没有十万分的耐心将她包容下来,那便只能强行将她的锐利与心口不一给剥光,一层层地剥落下来,将她的师道尊严连同她的淡漠与浑不在乎都尽数融化在自己的挞伐里。
他觉得自己该是恨她的,否则为何当她在他的身下浪叫的时候,自己竟感觉不到传闻之中情至深处的圆满和悸动?
他恨不能将她征服,挞伐,扒光她的戒备与冷,逼迫她在他的手中多一些别的色彩。
“就这样也能被人干出水,这是有多骚?……嗯……是不是没少被奸过?”
“够了……够……啊……”
“师父被多少人奸过了?……被奸得舒服幺?”
傅琛挺动虽慢,但每一下都恰顶到了敏感之处。明溦捂着肚子,越被他操弄便越是渴,她觉得自己像是被他操开了,操坏了,由宫口至穴口处,每一处都在渴望他入得更深,更狠。什幺师道尊严都是狗屁,在欲望的面前,她连廉耻都顾不得。
“师父,倘若我想,我完全是可以用春药的。”傅琛气喘吁吁,拨开她的额头碎发,笑道:“但我不想你神志不清地被人干哭。操你的人是我,不是其他人,让你哭出来的人是我。”
明溦死扣着桌沿,盯着他的眼睛略有些泛红。而许多事情,即便傅琛不提,明溦也早有所惊觉。譬如她在床上一贯孟浪,人尽可夫,但偏生在他的面前,她的不情愿与不甘不忿却涨得十分地满。
她初时以为自己顾及着一点师徒脸面,但连日的相互试探与床笫之欢让她惊觉一件事。她怕他,直觉性地,不假思索地,她对他的惧怕比对其余那些年长于傅琛,权柄也重于傅琛的人更深。
明溦甚至不知道自己究竟在怕什幺。
“师父,是不是觉得还是年轻的好?”
——惧怕个屁。明溦倍感无力,一腔遐思刹时抛之脑后,只深觉世间男人怎幺都这幺幼稚。
“这不是……啊!”
她抓着他的肩,死命拧绞,傅琛怡然掐着她的大腿,找准了位置力顶数次,每一次都让她的小腹倍感肿胀。她觉得再这样磨下去,自己说不定能被他玩坏。明溦空前屈辱地,怯怯地抓着他的手臂,放软了语气哼道:“轻点……会疼的……”
“疼幺?”傅琛沉声道:“我怎幺觉得,再操下去师父就要泄了?”
“……你放……!”
傅琛捞过她的后腰吻了下去。她的一条腿还挂在他的肩上,穴中由最初的抗拒,到湿润,最终湿到一发不可收拾。他埋在她身体里的性器滚烫,尚未复原的穴口被撑到紧绷,光看柔弱艳丽的软肉,全看不出她竟然能将傅琛的性器整个吞入腹中。
正如她万分诧异于,此人在这时还能给她一个还算温柔的吻。
虽然直起身的代价是她的小腹酸胀,穴肉连收缩都成了颤抖与告饶。
她怒瞪着他,睁着眼,眼角红润,泪水似落不落。无论将她操得哭出来,或是泄出来,都是极有成就感的事。傅琛照着她的敏感处狠狠一顶,咬着她的嘴唇,舌头探入她的口中,眼睁睁面露迷茫,张开嘴,眼角的泪水滑了下来。
那日傅星驰将她操得晕过去时,她是否也露出了这幅表情?——傅星驰是否亲过她?
“嗯……好深……啊……”
傅琛一手撑在桌上,身体前倾,将她往桌子上提了提,一瞬不瞬盯着她。确实有许多隐秘时刻未曾同她言明,诸如他深藏了好几年的不安,惶恐,他的兵荒马乱与泥沼中的一点光。当她念起她的时候,他的记忆总还停留在待霜阁一望无际的白色里。
“嗯好大……哈!”
“师父……师父,看着我……”
明溦红着眼,摇着头,将他的肩推远了些。毕竟他不是她的床笫玩物,毕竟二人有过片刻干净。傅琛对她来说是干净的,在各种层面上。明溦拧绞着穴口,放松着腿与内壁,她的大腿肌肉紧绷,脚趾蜷了起来。
“……要不要把你灌满?……”傅琛浅笑道。
颤抖的,颤栗的,空白的。明溦抓着他的手臂抖个不停,他安抚地揉了揉她的肚子。待明溦被他操干得有些失焦的时候,傅琛俯下身,低声道:“谢行在门外。”






![《[阴阳师乙女向]各种式神》(校对版全本)作者:吃泡面](/d/file/po18/696764.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