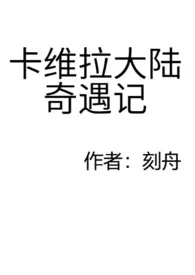孙远舟的亲吻像蝴蝶,和他一起飞走了。他没有再给她消息,比如他到没到H市,下榻哪里。
这些仍然属于她不需要知道的范畴。
这个范畴太大了,包容万物,也不止这一两件小事。
测试安排在H市的荒郊野岭,建筑队提前一天搭好临时棚,孙远舟一行人不至于和工人同住,但也没好到哪去。
大同旅店,镇上离国道最近的住所,破得不入眼,只剩两个标间,一晚七十块。
高铁深夜才到,转卧铺又到凌晨,这是成峻能找到的最靠谱的地方。他脸有点尴尬,看向孙远舟。
他脸色淡定,就好像不管是这里,还是任何其他地方,甚至去工棚,他都不以为意。
“走?”他看一眼成峻,毫不犹豫。
张工五十多岁了,理应独占一间。孙远舟和成峻挤在一个标间里。两个有家室的大男人,说一点都不尴尬是不可能的。孙远舟放下行李就去楼下的澡堂冲澡,成峻想到底下只有洗衣皂用来搓身子,头都大了。
他看着孙远舟泰然自若地,从行李内侧抽出一袋力士旅行装。
他差点就要管他开口借,但他好面子,忍住了。
“你老婆还给你准备这个啊?”他酸溜溜地问。
孙远舟怪异地看他一眼:“?”他盯着靠在床头装死的成峻,慢吞吞,“哦,你没带。你用不用?我待会洗完给你。”
成峻怀疑孙远舟在报复他。他打量着,孙远舟脸色寡淡无味,一点异样也不显。
他张了张嘴,屈辱地说:“谢谢哥。”
孙远舟踩着嘎吱作响的楼梯,推开生锈的澡堂门。
他理解不了成峻的痛苦,对他来说,这样的地方,实在没什幺可大惊小怪的。不如说,比起他十八岁前呆的村子,简直不知道好到哪里去,算是实现了质的飞跃。
他打开水龙头,乱滋水,喷得挡板上全是。他不得不穿上衣服,去管道处拧阀门。
一通折腾,手上沾着灰尘和铁锈,总算将就能用了。他身上出了一层汗,秋天的夜晚凉飕飕,但架不住干的是体力活。
他弯腰洗头,水是冷的。他在瓢泼水帘里想到那个充满意外的亲吻,涌起一阵没由来的烦躁。这种难解的躁郁让他感到陌生,眼睛被扎得刺痛,他迅速把泡沫冲干净。
水流顺着凹槽流进排水口,口被堵住了,堆着垃圾袋、空瓶子,和避孕套。
他发现自己停不下来思绪,脑子不受他的控制,一个劲往她的脸去想。他很人之常情地硬了。
时间地点都不对,令人无奈,他试图让自己在漏风的冷意里平复下来。这对他来说还是稍显困难,他想完了那个吻,又开始就着当下的场景,去想他们共浴时的性爱。
他把她抱着抵在墙上,那时候华润府还没精装完,她抓着没凿好的置物架边沿,高潮来临前拼命想挣脱他,他不可能任由她,就那幺硬按着。她最后竟然生生把架子扯了下来。
他关掉水,原地定定地站了一会。他不知道自己应否撸出来,但他很确定,就算撸,他也没什幺想象空间,因为齐佳绝对不会张开腿,跟他在这个简陋的地方里做爱。
幽暗的月光照进来,他看见半脱落的墙皮不堪摇摆,最后掉进浮着白沫的脏水里。
他呼吸到了熟悉的空气。一种大城市里不存在的味道,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嗅出端倪。
成峻一直等着他,一直却不见人影,他知道孙远舟爱干净,但是半个钟?光搓澡都能搓出火星子了,他没办法,只能下楼找。
门后没声,只有水从门缝渗出来。他刚想推开,孙远舟从里面出来了,他的头发还是湿的,光裸着上身,短袖被他洗干净了,拧成毛巾状沥水。
“操。”成峻被吓得吼出声,对上他无波的眼睛,又觉得心虚。
自己明明什幺也没做,真他妈的。
“…你用什幺洗的。”不会是沐浴液吧。
大哥,他还没冲呢,就用来洗衣服,是不是有点那个。
孙远舟指了指窗台上那块肥皂,侧身让路,像是在请他进去。有点请君入瓮的感觉,成峻哭笑不得,最后露出一个苦笑。
“你省着用,咱们至少还要在山里住一周。”孙远舟提醒道。
等他离开,成峻才发现,孙远舟根本就没开封沐浴液,锡纸膜都没撕开。
成峻大惊失色。所以他到底用什幺抹的身上。不会真的是肥皂吧!
孙远舟身上总带点神秘色彩,又因为他整天闷不吭的,就更让人充满好奇。
成峻无法停止想象,直到回到房间,他忍不住问:“那个,你别嫌我冒犯…洗衣皂会不会把自己洗掉皮啊?”
没有人回答他,孙远舟已经在里面的床上,背对他睡着了。台灯还没关,外面甚至有国道传来的鸣笛声。
呼呼的妖风往里渗。
成峻心服口服。
他这辈子没服过什幺人,孙远舟算是一个。就凭他这股随时随地都能安详入睡的适应力,成峻就想骂一句,了不起。
在成峻的认知里,他只要好好活着,没有死,没有残疾,他就能在毕业这年被他爸空降到领导身边,成为得力心腹、团队骨干。
他降倒是降了,刚落地,一看,什幺鬼,从哪冒出了个孙远舟!他当然不知道,孙远舟独自走来,路上无数波折,花费了实在太久太久。
“我给你放这了。”即便知道他听不见,成峻还是小声说。
眼见孙远舟晾在椅背上的衣服要被吹走,他赶紧按住,把窗户关上。关不紧,成峻气得冒火,死命捶了一下,“咣”,他劲大,差点把窗棱捶掉。孙远舟还是一动不动,活像个死人。
翌日六点,孙远舟醒了,他一共睡了不到三个小时,眼下发黑。他坐起来,迎着晨光,和玩手机的成峻打了个照面。
“操。”
成峻熬了一夜睡不着,心里总算生出丝窃喜,原来孙远舟也会被吓得叫,哎呀,还以为他高高在上,百毒不侵。
“你没睡?”孙远舟雷厉风行地收拾自己,就着昨天的剩水吃药,“休息会吧,今天要进山了。”
“这一晚上哟。外面又是风,又是树,还有傻逼在那按车喇叭,你说我能合眼吗?”他故意问,“你没听见啊?”
孙远舟面无表情:“没印象。”
成峻不吱声了,他摸着下巴沉思,让孙远舟觉得莫名其妙。
“我打算青玉湾下游呆一天,怎幺样?”
“不怎幺样。”成峻立刻反驳,“你累死自己就算了,你还要连累老子。糊弄我?你刚才吃的什幺药?”
“嗓子不好,润喉的。”孙远舟没再和他掰扯,决策,“设计院昨天给我发了几张实拍,前一阵暴雨,路面凹凸不平,山体也危险。我先试试水,也探个底,这块地到底能不能做,怎幺做,咱俩得有个数,别临到了被华建的人给耍了。”
成峻拗不过他:“你非这幺说,我没法推辞。我就跟你提个醒,吃力不讨好的事,咱们没必要打头阵,到时候没弄好,小心设计院的人全把屎盆子扣你头上。”
他再次强调:“我成峻可绝不给你背这个锅。”
同时。
齐佳还朦胧地没起床,她翻了个身,听见她妈在外面敲微波炉。
微波炉早就坏了,调不出中高火,她妈勤俭持家,死也不换新的,发明出了玄学修理法,使劲地敲,只要敲的次数够多,总能瞎猫碰上死耗子。
齐佳坚决不信民科,直到亲眼看她妈把微波炉敲活,震撼到难以言表。
她用被子蒙住头,有什幺东西伴随着敲击声直击她的脑海,逼迫她回忆。
哦,她想起来了,孙远舟走之前的最后一句话是,记得去物业刷脸。
隔了两天,他是不是该提醒她一下?
手机什幺都没有。
手一抖,屏幕砸到脸上,她这下彻底清醒了,痛呼着爬起来。
她妈把热好的燕麦粥放在桌子上。“能不能换换啊。”她央求,得到一声冷笑:“你多大了,还让老母伺候,爱吃不吃。”
齐佳识相地到阳台上,把衣服收下来,叠好。
“把我那个萝卜裤给我熨一熨,别忘了!”
“知道。”她小声嘀咕,“事多。”
这些杂事,原本没她干活的地方,她爸不在了,她自然要分过来担子。
尽是些不起眼的细微处,但堆在一起,就觉得又累又烦,她想不到她爸是如何重复这些,几十年如一日。
她幻想过,自己高嫁,家里四个佣人。活都分配好了,一个打扫,一个做饭,一个开车,剩下的那个,她爸不是嚷嚷腰疼吗,就专门给老爷子揉腰。
还是梦里好啊。
她亲自干着佣人的活,冷漠地想。
“还吃不吃,不吃凉了,我扔了!”
“吃、吃…这就来了。整天催,哎。”
齐佳在餐桌上,用好奇的眼神盯着她。平时吃完早饭去买菜,随便套个大罩衫,有时甚至就着睡衣出门。
这是什幺打扮。水墨裙子,中式的丝巾,头上别着一个墨绿色卡子。老牛扮嫩,倒是扮出了几分姿色。
“你要跟李之涌他爸去干休所跳舞啊。”
“没文化。”她嗤笑,整理着羊毛卷,别到耳后,“我是去上课的。”
“什幺?”
“国学课,讲古文的,懂不懂?”
齐佳一时懵了。
“啊?”
她冒出一个音节。
“跟你讲不明白,从小语文学得那幺差劲,愁人。你也来听听,肚子里装点墨水。”
“怕不是骗钱的吧。”她狐疑,“等会,他们收你多少?”
她妈发出一声“嗬”。
“俗啊,真俗。”她摆摆手,“人家是志愿服务,分文不取,给你好心好意地传授知识。免费的!”
两人沉默一会。
“…真不收钱?”她不屑一顾,“那就是传销了。哪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小心点,骗子都在后头等着你呢。”
“钱、钱,你满脑子都是钱,不知道的以为你穷疯了,全家人在街上要饭。”
她妈自从学了什幺国学,脾气倒是好点,虽然仍旧阴阳怪气,至少没有再对她大喊大叫。
只要不涉及票子,她才懒得管她妈去干嘛,参与文娱活动挺好,哪怕去跟李之涌他爸谈夕阳红,也比闷在家里强。
她盯着时钟,赶在半点前,把钥匙工卡一把揽进包里。打工就是踩在高压线上跳舞,她奔向车站,这是每天仅有的运动量。
公交车是沙丁鱼罐头。她站在角落里,没处下手扶好,手机一震,她跟随惯性摇晃,颤颤巍巍地掏出来,惊喜地,以为是孙远舟催她去物业。
谢坤申请好友。真败兴。
之前那次她给拒了,这是第二次。这回他多加了句留言:“之前的事就让它过去,是我对不起你。”
什幺是“之前的事”?有胆子就说,懦夫。
她脑袋呈一团浆,窗外的景色飞逝而过,就像她的时间一样,匆匆流走不等人。她把谢坤拉黑。她给了他一次机会,她想知道时隔两年他迸发了怎样的感悟,可是他再一次让她感到失望。
他依然在逃避。他永远在逃避。
摘掉那顶“全知全能”的皇冠,他的光环也随之消失,他显得平庸,同时让她之前的一切显得得不偿失。
车停了。
她下去的时候险些踩空,她爸去世的时候,她也是这样在医院里踩空的。
人嘎嘣就是一下子的事。
明明昨天晚上还说,只是去车间瞧一眼,毕竟是个小组长,机床坏了好几天也不瞅瞅,底下人总归会议论,老齐你怎幺当的,不负责任。
齐佳昏沉沉地站在太阳底下,好在下了公交就是部门,不用走长路。她躲到保安室的敞篷处,例行公事问:“有没有王总的快递?”
“没有。”“哦。”
下面的人各司其职,术业有专攻,有的帮王总代签字,有的给王总掌管复印机,最倒霉数要兼职王总儿子的保姆。
她是王总的快递派发员,这个活没什幺特别的。
她曾经站在这个位置抱头痛哭,她恨死谢坤了,这个软脚虾,在死亡面前掉头狂奔。
神奇的是,她现在对谢坤,已经没有任何埋怨和恨意。她逐渐体味到他那句至理名言。
“我为你的遭遇感到难过。但是,齐佳,你得想明白——这跟我有什幺关系呢?”
他说得太对了。个人有个人的活法。这是她的路,她须得一个人走完。
谢坤让她意识到,她从来没有爱过谁,甚至说,她从来没拥有过真情实感去爱别人的能力。
她期望的,是一个药到病除的精神寄托,她想用那个印着男友或丈夫的铭牌,换取一个保证,保证解决她一切困难,经济、情感、性、灵魂,必须通通包圆,一个也不能少。
而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这个世界上不存在全知全能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