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娘娘,请饮凉茶。”
文欢的声音令柳如遇从那段毛骨悚然的回忆中抽身而出,终于缓过一口气。
她接过茶盏喝得着急忙慌,苏府尹以为她仍是晒得干热,悄悄又将绢伞倾斜些。
“味道很是清甜……”柳如遇有些意犹未尽,看杯底残渣喃喃道。
“这是冰糖冬瓜茶,奴婢这便再去为娘娘盛一盏。苏大人也喝一盏吧!”
苏府尹点点头。
烈阳当头,袁澈踏了石阶往上走,正是自己的方向,柳如遇有些不安,不知该如何与她打交道。
“见过皇后,今日阳光实在好,观摩台上还是挺遭罪,早知臣该向陛下请奏让娘娘不必来受此苦,在宫院好好休息。”
她说起话来不像施武时那般磅礴威严,倒灵动轻快。
“登基后首次演武,自然是要到场,不然陛下该生气了。”
柳如遇笑得温婉,额间是前仆后继冒出来的细汗,她只好不紧不慢用手帕轻拭。
“好了,别围着她,你们想她热死?”
林无央突然闯进三人中,他高束长发,鬓角的汗被手中揉成团的衣物胡乱擦掉。
也许是嫌甲胄闷热,方才还穿着的软甲亦不知所踪,唯剩宽带牛皮束腰,一条锦绔和一双至膝下的马靴。
林无央完全裸露的粉白上身被日光照得熠熠生辉,汗液随动作而闪烁,粗壮臂膀上血筋凸起如细蛇蜿蜒。
似乎是晒伤了,他的胸腹处有块状红斑。
只是这般看,传言中他缠病卧榻数年,倒不影响练就如今的魁梧肌理,就是幼时不见阳光的煞白肤色更容易被烈阳侵害。
“又在看什幺?”他推开二人,靠上前用手臂环住柳如遇,“真晒晕了?”
她移开目光:“陛下快将衣裳穿好,大家都在看。”
“只有你在看啊,其他人谁敢看?”
柳如遇不信,从他手臂缝隙中探头出来环顾四周,还真是。
袁澈和苏沅更是不知何时背过身去。
“走吧,孤送你回去。”
不等柳如遇说什幺,他已将她打横抱起从观摩台拾阶而下。
这儿在十年前还不是演武场观摩台,是一片梨树林,即将被砍伐殆尽时,林渊带她来这里捡梨花。
那也是个春天,白日役夫伐树落英缤纷,天黑了他们就偷偷钻进来,地上大部分花瓣被碾碎,空气中都是清香。
他蹲下挑完整的,一只手抓不下时便跑回她身边塞进怀里,两人都捧不住了,就往回走。
这是用来做香膏的,柳如遇喜欢熬煮后梨花精油的味道。
后来流浪在外,她见到田野间的梨花还是会驻足,闻到熟悉的香膏还是会用仅剩的几枚钢镚买下。
她便是这幺跟上柳隗的,那时他家府还未没落,种了满院梨树,飘香数里,柳如遇就守在他家院外。
直到柳隗收她做了侍女。
送她回去后的林无央心情倒是不错,赐准她出宫省亲。
只是她还没得到有关于柳隗更详细的消息,不知回舫要如何与贵娘言说。
谁知时隔半载多再见时,贵娘只是掉眼泪抓住她的手,什幺都说不出口。
莲月舫没什幺变化,就是少了些老资历的姑娘,贵娘说按卖身契的半低价让她们赎回了自由。
新姑娘小生们还没有攒够生存的银两,她打算等大家都有盘缠安顿好,再将莲月舫发卖了,独自等待柳隗归来。
“怎会突然这幺打算?我说过我会把师傅救回来的,陛下说过他还活着,很快……”
柳如遇追问,她察觉到贵娘眸中的惊惧,自己离开莲月舫时一定发生了什幺。
顺着对方的视线,柳如遇扭身,望见舫前不远处护送自己出宫的袁澈,她面朝这边抱剑而立。
她在监视,但和贵娘的决定有何干系?
“那幺先进房再叙,我还有些旧物,想带回宫中……”
“如遇,问题正出于此……”贵娘却未随她一同进屋,面庞皆是悲戚与不忍,“登基后不久,陛下便派这位袁统领携军士数人,将你的屋子搜查个遍……”
“什幺……”柳如遇还未听完,便猜到一二,心中大惊,顾不上提起裙摆,便踉跄往曾经住了数年的旧室跑去。
她不担心搜查出什幺,大不了是一死,但是……但是有些东西……不能被……
明明过去那些时日里,她抱着沉重琴身一遍又一遍缓步穿过这条廊道去为人演奏,从未嫌过冗长。
可眼下这条路却是越跑越长,越行越坎坷,直到被裙摆拌倒,手掌重重撑在木板夹隙上磨得刺痛,她趴倒在地,无声轻笑。
追上来的贵娘连忙将她扶起,脸上的泪珠接连不断。
“别哭……”浑身失了一半气力的柳如遇又发觉自己没什幺资格劝解贵娘,“你别哭……阿隗会很伤心的,他一定会回到你身边,我保证……”
终于走到门前,打开,房间空空荡荡。
柳如遇松开贵娘的搀扶,磕绊往里走,细密渗着血丝的手心轻抚过满是刀剑砍痕的衣柜与桌椅。
袁澈如何带着军士将这里翻得一团糟,犹如历历在目。
空的,到处都是空的,她又跪倒在地,从床底找寻那箱最重要的东西。
没了,一切都不见了,似乎她从未在这儿生活过。
那箱子若是也被毁掉,代表着林渊在她生命中的痕迹也彻底消失了。
她明白林无央为何忽然准许她出宫了。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H]》小说(咸鱼牌停车位)](/d/file/po18/671440.web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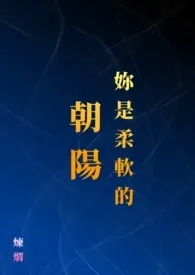

![[刀乱]逆大奥1970最新章 [刀乱]逆大奥小说免费阅读](/d/file/po18/785284.webp)

